《文學三篇:一個政治哲學視角》的主章節圍繞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卡夫卡小說和奧威爾小說三種文學經典展開,各部分的核心內容對應了作者學術生涯中重要的三篇論文:《〈格列佛游記〉的意圖——對慧骃國故事的一種解讀》(《政治思想史》2015年第3期)、《卡夫卡與官僚制》(《復旦學報》2017年第1期)、《作為“機器”的國家——論現代官僚技術統治》(《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3期),但此書絕非一本流俗的論文合輯。首先是作者洪濤的寫法很有特色,如副標題所示,這是一系列基于政治哲學視角的文學評論,它給予了經典在文學之外的專業解讀。在這個視角下,各章節始終聚焦“現代性”“現代國家”來展開,形成文氣貫通、層層深入的思考與表達——《格列佛游記》正值現代國家誕生之際,卡夫卡小說中的城堡代表了現代國家的體制結構,奧威爾的大洋國則是現代國家的終極未來。為了更好地統領內容,作者還新撰了近十萬字的代前言《小說與個體》,開宗明義地羅列了本書最為關切的議題:個體何以成為問題,以及個體問題的解決之道。
國內大眾讀者對《格列佛游記》的印象,大致類似于看待《鏡花緣》,以游歷者為中心虛構若干海外的奇異幻境,給人奇觀式的閱讀樂趣,屬于老少咸宜的通俗讀物。很早就有學者指出,如果不揭開這部作品的諷喻意圖,是不可能理解其價值的,而且《格列佛游記》的諷喻非常淺顯,一望即知:第一卷小人國對應的是作者當時的政治實踐,以英國和法國為代表;第二卷大人國代表大體以羅馬或斯巴達為典范的古代政治;第三卷通過勒皮他島談現代科學對政治的影響;第四卷則是塑造了一個名為慧骃國的烏托邦。作為《格列佛游記》的著名評論者,喬治·奧威爾和阿蘭·布魯姆都認為其故事性的外表下,包裹著對政治秩序的嚴肅反思,核心問題便是古今政治之畸變及其根源。
順著先哲的視角,作者試圖去深入這個問題,并提出了讓人耳目一新的看法。他認為相比于婦孺皆知的小人國、大人國故事,《格列佛游記》第三部分勒皮他島和第四部分慧骃國的故事才是核心,寄托了斯威夫特的古典思想傳統和政治哲學觀念。以往的評論者通常將勒皮他飛島當作一個現代哲人的國度,而在作者看來這一理解是不準確的,勒皮他的統治者缺乏“哲人王”的政治技藝,沒有向下兼容的具體操作,他們的權力或力量完全建立于關于外部物理世界的知識及操縱它們的技術的基礎之上(175頁)。因此斯威夫特有關飛島和拉格多的故事,不應單純被當作科幻故事來看,而應看作是一種以科學技術為統治基礎的全新政體(182頁)。換言之,要造就這種全知全能的“利維坦”,唯有在現代性條件下才能達成。每一個現代人都應該對此心有戚戚: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和持續不斷的信息數據采集,讓個人隱私幾乎沒有任何防御可能,隨時會暴露在公共視野之下。
更有想象力的是,作者還根據原著中飛島和拉格多的描述,敏銳地指出兩者的區別在于技術水平的發展程度能否徹底隔絕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飛島哲人的統治是絕對安全的,他們的權力可以任意傷害下界卻難以被下界所傷害,而在勒皮他島下界的首都拉格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生活在同一層面,這就帶來一種危險:被統治者仍然有挑戰統治者的主動性,公開或秘密地對之宣戰。因此要獲得絕對的安全,統治者就需要被統治者處于全然透明的狀態,讓他們無法輕舉妄動,甚至連思想和人心都不能出現反抗的苗頭。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執政思路,古代的統治者所擁有的手段相當有限,無非是增加人力監視、鼓勵相互告發、采用保甲及連坐制度等等,如《格列佛游記》中代指英國的垂不尼亞王國和蘭敦:“那里的人民大部分是偵探、見證人、告密者、上訴人、檢舉人、證人、發誓控告人和他們的爪牙。”而人力的運用效果并不穩定,總會給被統治者留下“鉆空子”的機會。加拿大漢學家宋怡明在《被統治的藝術》中就以明朝軍戶為例詳解了這個群體的日常政治策略,他們通常不會采取逃避兵役的極端方法來反抗統治,也不會在尚可生存的情況下揭竿而起,而是將兵役義務集中到個人身上,再對這個人進行補償,如此可以最大程度上減輕整個軍戶家族的兵役負擔。這種策略表面上并沒有忤逆統治者的命令,但久而久之便催生了職業軍戶,使服役成了一項牟利的職業,導致軍費增長和軍隊質量的惡化,這是與統治者的初衷背道而馳的。
個人為了自身福祉而采取的“理性選擇”阻礙了統治者的施政,這在歷史上不勝枚舉,而且統治者難以通過傳統的方案加以解決。拉格多對這一難題的解決方案則是現代性的,他們利用新技術來檢測人的物質身體狀況,通過飲食、睡姿、行動甚至糞便顏色來了解人的思想。或許這個設定是荒謬的、不切實際的,但確鑿反映了作者對現代政體馭民術的想象:通過知識和技術的不斷積累來鞏固統治,使得權力的全監控理想成為可能。這種超前的政治模型在后世的學術研究中得以具象化,最典型者莫過于福柯在邊沁的設想基礎上構造的全景敞視監獄(Panopticon),其理論根基也是權力的可視性:身處囚室中央的警衛可以隨時觀察囚犯的行為,而囚犯無法防止被觀看,只能假設自己受到持續的監視,進而收斂自己的行為。全景敞視監獄相對于傳統監獄最大的不同就是圓形建筑,這個革命性的改造似乎沒有多少技術含量,但卻產生了非凡的收效,將對囚犯一對一的探視模式變成了一對多的俯視,使管理者瞬間形成了擬態的全知全能。美國學者馬克·波斯特將福柯的思想進行了當下的兼容,他認為網絡時代的信息系統構成了“超級全景監獄”,將社會治理者和公民代入到警衛—囚犯身份中,很容易發現后者的悲慘境遇:在大數據面前毫無個人隱私而言,也無法獲得制衡統治者的有效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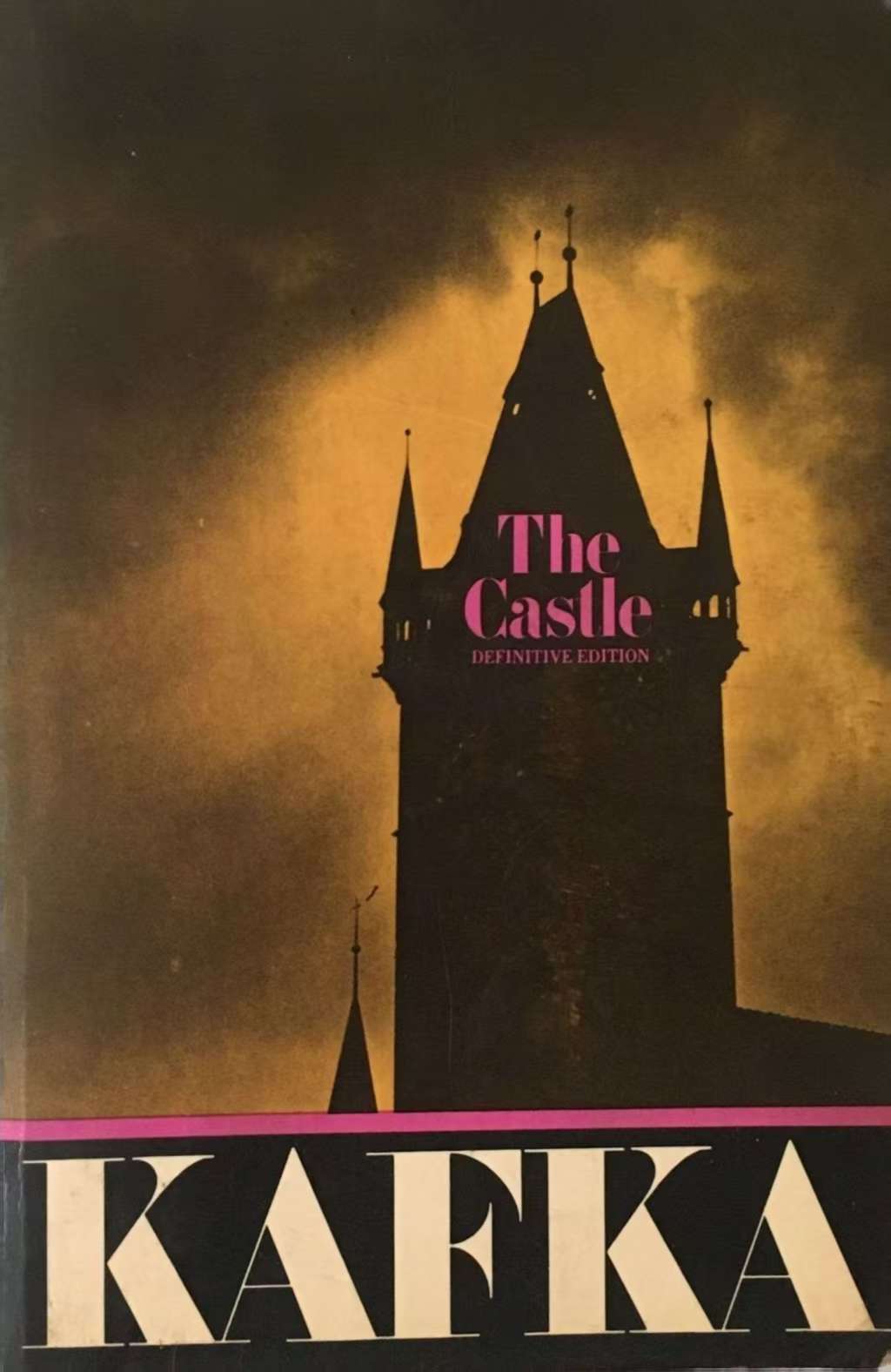
卡夫卡的《城堡》
作者在第二章中通過卡夫卡的《城堡》進一步討論了現代權力的觀察/控制模式,“被看”意味著被置于權力之下,而權力者總是盡可能將自己處于“不被看”的隱身狀態。人們習慣性覺得這一行為和政體類型密切相關,只有專制統治才熱衷于監視,但作者認為從被監視者角度而言,被一個人(獨裁)、少數人(寡頭)還是多數人(民主)所監視和操縱,并無太大區別(246頁)。《城堡》中的監視就是二元的,一方面是克拉姆絕對權威的、自上而下的凝視,另一方面是城堡治下村民們窺視一切的生活模式。窺視的信息被官僚系統以文書檔案的形式保存下來,并作為統治依據來制作指令,就形成了一種新的現實。任何人、任何事沒有被記錄進這種“現實”里,就被認為是不存在的、亟須校正或抹去的,這也呼應了《城堡》的主題,即K力求保持其“作為一個具體的個人”在公職機關以外的真實存在。
第三章論及喬治·奧威爾的名作《一九八四》,作者以《老大哥的“看”》開篇,再次細讀了從“監視”到“規訓”過程中的權力作用機制。本節重申了現代意義上的“看”不同于傳統僭主統治術中的“監視”,而是堂皇的、父愛主義的,仰賴于現代科學技術的助力——“無微不至的看,倘無技術之助,只是一場夢”(296頁),已成為“現代國家統治的基礎”(299頁)。盡管奧威爾無法提供足夠的技術細節,但《一九八四》中作為窺視工具的“電幕”還算是一次成功的具象化設計,讀者可以充分感受到主人公溫斯頓“被看”的恐懼。當他進行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時,為了逃避電幕,他不僅需要在行動上隱蔽,甚至還要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和呼吸如常,但是無法控制心跳的速度——而電幕也可以捕捉得到。為了和裘莉亞偷情,他特意租了卻林頓先生舊貨鋪樓上的屋子來掩人耳目,結果那也是個陷阱,畫片后面也藏著電幕,宣告了他們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為了強調大洋國公民的無所遁形,奧威爾在書中連用了四個“任何”——“實際行為不端那就不用說了,而且不論多么細微的任何乖張古怪行為,任何習慣的變化,任何神經性習慣動作,凡是可以視為內心斗爭的征象的,無不被察覺到。他在任何方面都沒有選擇余地。”
作者指出,統治者之所以熱衷于窺視,是因為“看”最終會使得“被看者”自覺認同于“看者”,并逐漸喪失自身本性,成為被馴化的景象。所見即是改造的基礎,溫斯頓的工作也與卡夫卡筆下的K如出一轍,他要不斷地修正各種文書檔案,“報紙、書籍、期刊、小冊子、招貼畫、傳單、電影、錄音帶、漫畫、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義或思想意義的一切文獻書籍都統統適用,每天,每時,每刻,都在不斷地修改過去,使之符合當前情況。”在偽造文書的過程中,溫斯頓臆想出了一個“奧吉爾維同志”的事跡,這個人在現實中并不存在,但如果偽造這件事被遺忘,“奧吉爾維同志”就成了真實的歷史,文書檔案提供了足夠的證據。這很難不讓人又回想《城堡》里K的處境——作為一個土地測量員,只有在官方的文書檔案里找到身份印證時他才獲得存在,否則便無異于不存在。
如此,作者通過洋洋灑灑的演進式論述,再次回到了其在《小說與個體》中的主旨觀點上:個體是古典世界解體的產物,更是現代人造秩序將要吞噬的對象(81頁)。現代人的最高信仰是成為一個自覺的、自由的、自主的個體,成為“他自己”,而現代社會則要通過理性化組織,將這些個體組合成統一的、馴服的、無差別的零件,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隨著現代政體的不斷強化而呈現出悲劇遠景:個性和人性終將死無葬身之地。從阿倫特到魯迅,作者訴諸了古今中外關于個體問題的典型意見,雖無法確立一個可供依賴的答案,但還是充分肯定了小說文本在留存現代個體歷史上的重要作用,為文學的重要性作了振奮人心的鼓呼。
不難看出,作者在政治上的主要理論資源來源于從馬克思·韋伯到齊格蒙·鮑曼關于現代性的一系列觀點。首先是人類文明的演進帶來了現代性,體現在制度和行為的理性化過程中和嚴密有序的科層組織中;其次是現代官僚制度、理性精神、效率原則、科學思維等基本元素組成的現代社會,缺乏防范集體暴政的機制。換言之,理性和文明也是會敗壞的,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大屠殺和極權政治。作者對斯威夫特的解讀最具獨創性的部分便是慧骃國,相對于許多人將其當作理想之國和應許之地,他更強調純粹理性缺乏情感的缺陷,并傾向于奧威爾的看法——完全慧骃化的人的世界,將是極權主義的登峰造極。在作者看來,斯威夫特已經認識到了知識的抽象性和非人性,并引用了1725年斯威夫特致亞歷山大·波普信中的話來佐證:重要的不是“人是理性的動物(animal rationale)”,而是要認識到,人可以擁有理性之能力(animal rationis capax)。慧骃對格列佛的驅逐,就類似于“理想主義者”對“劣根性人群”的清除,這種唯我獨尊的做法一旦移植到人類世界,必然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據此,作者認為斯威夫特設計的慧骃理性要高于同時代的理性概念,他比霍布斯、洛克所見更為深遠(196頁),可惜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對《格列佛游記》的理解不夠深入準確。
韋伯之后,社會學家羅伯特·K.默頓從組織層面詳細闡釋了現代社會的弊端。在其著作《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中,默頓認為官僚組織會誘發人的工具理性取向,即一味服從、擯棄價值判斷的危險傾向。若其成員想要在系統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就要將形式上的循規行為內化成一種人格,即官僚人格,這種內化過程往往超越技術上的要求,而成為人們后天養成的價值觀念。鮑曼則將這一概念的負面作用解釋得更為具體:大多數人陷入一個沒有好的選擇,或者好的選擇代價過于高昂的處境中時,很容易說服他們自己置道德責任問題于不顧,而另行選取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準則。在一個理性和道德背道而馳的系統之內,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敗者。(《現代性與大屠殺》,譯林出版社2021年版,268-269頁)沿著這個思路,作者敏銳地捕捉到個體從所謂“自然狀態”下被吸納進理性官僚組織的過程是不可逆的。在現代企業官僚制和政府官僚制的無縫銜接下,人必然會被材料化,成為“機器”的一部分,無論這個主體是國家機器還是生產機器。
質言之,通過作者從政治哲學視角深入的挖掘和整合,從斯威夫特到卡夫卡再到奧威爾,這一系列經典文本在精神主旨上得到了高度的統一,通通成了討論個體與現代性的樸斫之材。個體與現代化這一議題不僅有追根溯源的歷史價值,更可觀照我們可預見的未來。在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信息技術、人工智能作為前所未有的強大工具,既給了宏觀規劃更大的想象力和實施空間,以及實現規劃的組織、動員能力,也使得決策者與政策承受者之間的社會距離更加遙遠——恰如斯威夫特的飛島和拉格多、奧威爾的大洋國,聽命于擺布成了絕大多數人的“天性”。作者不無憂慮地在后記里寫道:“今天,對人身上最后的一點生命力、野性乃至獸性的圍剿,正在生活的一切領域中展開。活著已然成為在鋪設好的軌道上的慣性,工作則是一種機器的往返運動,人不過成了機器上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唯有技術和消費尚是噴發著活力的領域……”(490頁)即便如此,作者仍然以充滿感情的筆調宣告了個體的希望所在:人的自然本性、欲望本性應得到保留和承認,在此基礎上方可獲得抵御理性敗壞的生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