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午餐會是學術界常見的“非正式”學術交流方式,無論是普林斯頓高研院、哈佛—燕京學社,還是國內眾多高校和研究機構,都經常采用這種開放自由的形式開展討論和對話活動。在溫飽之后轉而追尋美食和精神愉悅,似乎是刻在人類基因里的天性,作為他人的精心呈獻之物,美食如此,知識亦然,兩者皆不可辜負。
南京大學“學術午餐會”的傳統由來已久,最早開始于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先生在2005年發起的學術冷餐會,到目前為止已經舉辦了一百多場。今年,南京大學出版社打造的“南大讀書人”文化空間正式啟動。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新生學院聯合開展的“學術午餐會”延續了南大讀書文化的基因,邀請歷史、哲學、文學、社科等領域的學者,帶領來自新生學院的本科生們共讀學術著作,讓同學們接觸到一流的學術資源,培養他們的閱讀興趣和學術素養。
本期活動,南京大學哲學學院的藍江教授為同學們講評《規訓與懲罰》和《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兩部學術論著,重審現代社會的組織方式。以下是藍江講評的文字稿整理。

藍江在活動現場
現代社會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兩個部分,實際上都沒有那么理所當然
我們從古代社會、封建社會過渡到今天所謂的現代社會,也可以叫資本主義社會,中間發生了什么變化?我們可以用“理性”“啟蒙”等詞匯來描述現代社會是什么,但是這個過程中,有一些關鍵性的東西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一個是人,《規訓與懲罰》跟我們講的就是人在從古代社會步入我們現在的這種以規范為主導的現代社會的時候,發生了一個變化,那么它是怎么發生的?當然我們可以按照一種講神話的方式說,這是人類啟蒙、人的理性自覺自律以后形成的,這是康德式的說法。但是福柯在《規訓與懲罰》里,實際上不止在這本書里,在他早期的其他書,比如《古典時代瘋狂史》還有《臨床醫學的誕生》里,他仔細分析了現代人是如何從這樣一些概念中間脫穎而出的,其中一個就是我們把一些不符合理性概念的、不符合理性規范的人給排除出去,比如說把瘋子、病人、囚犯給排除出去,然后在囚禁的過程中產生了規訓的模式,實際上是在規訓的情況下,生成一個被規訓的現代人。我們現代人除了有理性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叫“守規矩”。這個概念不是人的自然本性,而是在社會中被塑造出來的,是有一定條件的。福柯就用了一本書告訴我們人是如何從一個散漫的、偷懶的,或者是不符合現代屬性的人,變成一個可以在現代資本主義體制下進行生產活動的人,這就是《規訓與懲罰》。
第二本書是西蒙東的《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西蒙東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技術物(technic object)。這個概念與他之前的博士論文有關, 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這兩個概念是形式/形態和形成,information實際上是有信息的意思,但它也有一定的意思是使之獲得形式,我后來翻譯成“賦形”,即獲得個體化。西蒙東的意思其實跟福柯很像,我們每個人實際上都有一個“前個體”的過程,不是一開始就是個體的。在現代社會之前,是以“前個體”的形式存在的,在現代社會才被個體化為大家現在理解的獨立的、自主的“個體”概念。這個個體概念與另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有關,就是技術物。西蒙東寫了那本《從形成和賦形來看個體化》以后遭遇了很多爭議,所以他被迫要用一本新書來回應這些爭議,就是他的《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我們跟自然打交道,究竟是直接與自然打交道,還是要通過某種技術物來打交道?這個技術物是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獲得連接方式的一種途徑,這就叫technic object。
這兩本書跟我們解釋了,現代社會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兩個東西,實際上都沒有那么理所當然,一個是人,規訓的人,第二個是物,技術物,這兩個構成我們現代社會組成的兩個部分。
現代社會給人的感覺是普遍性的控制,這個問題靠個體的防范是無解的
所謂的反抗意識,也是在規訓社會上被建構起來的,你不可能在一個建構的籠中去建構一個反抗整個體制的意識。舉個簡單的例子,同學們不想學習了,給大家放幾天假,你們會發現自己所做的事情仍然屬于被社會高度控制的階段,比如你要看電影、出去郊游、睡懶覺,或者打游戲,其實根本就沒有逃脫整個社會控制的困境,所謂的反抗實際上是無力的。反抗以后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生活,是不是談不出來?很多時候,即使給了你時間和空間,但實際上想象不出來,除了現在這個巨大的社會基礎空間,我還能做什么?我想要的是什么樣的境況?這是剛才談的核心問題,就是規訓社會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每個人認為自己最獨特有趣的地方,實際上也是在規訓社會或者是“全景監獄”社會中被建構起來的。現代人的生存,屬于悲劇性的邏輯,大家是不是非常認可這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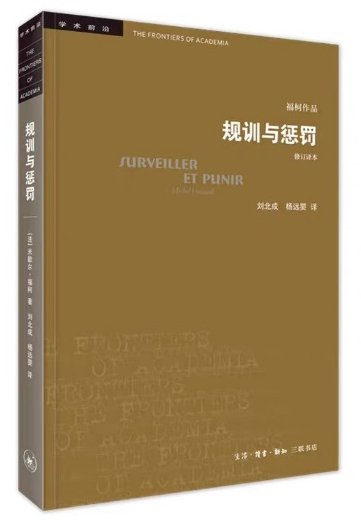
《規訓與懲罰》 [法] 米歇爾·福柯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三聯書店
我們再回到剛才同學說的歷史性的問題,他提到福柯發明了一種研究方法,叫譜系學(Genealogy)。福柯在《詞與物》和《知識考古學》中重點去談這個問題,他把考古學(Archaeology)和譜系學(Genealogy)放在一起,嚴格意義上不是歷史學,而是譜系學。他把很多的歷史插片、很多歷史事實放在一起,并不是像我們寫大的歷史現實那樣,給出一個歷史“主旋律”。像我們寫《三國演義》,開始有一條“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就是我們中國歷史敘事的一個主旋律,然后你再去看所有的碎片都是按照主旋律來展開的;比如我們講歷史唯物主義,講歷史總是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最后到社會主義社會,這也是一種主旋律。
而福柯沒有給出主旋律。我們講從懲罰到酷刑,再到規訓、到最后的“全景監獄”,這里沒有主旋律,沒有一個主導的對手去支配它,實際上它們是沒有連續性的。福柯只是把不同時期的、從17世紀到18世紀的歷史材料擺在一起,讓你自己去得出結論,這也是福柯很雞賊的地方。他沒有給你一個畫外的評價,而是把很多現成的歷史材料堆砌在一起,讓你自己從他堆砌的這些歷史材料中間,得出“現代社會正在日益走向大監獄”這樣一個問題。他并不是展現出、提出一個連續性的問題,說上個階段必須隱含了下一個階段的發生,在全書的幾個章節中間實際上沒有這種情況發生。不僅在這本書里,福柯寫《古典時代瘋狂史》,寫《詞與物》,寫三個學科的誕生都沒有用這種方法,而是把很多歷史切片像錯層一樣堆在這里,這種譜系學的方法是福柯的一個特點。
為什么說我們今天的“現代社會”是被建構起來的?“現代人”具有的觀點是通過我們的身體方式,而不是通過意識方式建構起來的。福柯為什么講酷刑?因為酷刑和身體的守規矩是成正比的,身體上守規矩以后,人們才知道反思,如果說有哲學的話,它告訴我們為什么要守規矩、怎么去守規矩,守規矩的話就免遭酷刑。任何囚犯,他之所以會守規矩,是因為有身體的懲罰存在,最后從他人的懲罰過渡到自我的規訓。在全景監獄中間其實根本就看不見看守,但人們為什么依然守規矩?是因為我們害怕懲罰,這個東西就變成了全景敞視監獄的“看不見的”看守,迫使我們不得不去守規矩。
今天我們這個社會比福柯的“全景敞視監獄”更加panopticon,這個詞是邊沁發明的,pan是“泛”的意思,optics是“光學”,panopticon就是“無所不在的光照耀在大地上”,你們沒有任何隱含的空間、任何應用空間去實施你的自由意志。我再稍微延伸一下,福柯有個很重要的隱喻,講人的一生是有在“光的前面”和“光的后面”的區分,在權力面前我們把它叫光(light),在權力背后就叫影(shadow),你所有的叫free will的東西只有在shadow上面才能實現,在光的面前是無法反抗的,因為權力的陽光直接照下來。那么全景敞視監獄實現了一個什么樣的領域?就是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任何shadow了,沒有任何可以讓你自由實施自己行為的方式,只有權力的光去照你,必須讓你的所有行為都符合規范,這就是所謂的現代人的行為。最后一章第一句話,“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大監獄”,他并不是真的在寫監獄,只是通過監獄這個領域來說明我們現代社會每個人都是按照監獄模式來執行的。
去年讀書會,一個同學也是講《規訓與懲罰》,他說他讀福柯,最讓他聯想到的是什么?是他們坐在教室里,班主任偶爾從窗邊露出的目光。頓時全班都整整齊齊認真聽課,原來想睡覺的、想打牌的都一下子老實了。他特別能體會到那種全景監獄的感覺。這就是現代社會的感覺,因為有一個看不見的目光,通過攝像頭、通過各種各樣的竊聽設備、通過監視控制,讓每個人都像有個班主任在后面盯著我們看一樣,在拉康那里叫“大他者”,一個Other盯著我們,所以我們的行為必須要守規矩。
這個社會給大家的感覺就是普遍性的一種控制,比如說剛才你們提到了德勒茲的“控制社會”,這個概念是在德勒茲《哲學與權力的談判》這本書的最后一章出現的。還有同學提到了韓炳哲的兩本書,一本是《透明社會》,還有一本是《倦怠社會》。福柯那個時候研究的還是建筑的問題,今天已經是無所不在的電子身份,和我們人已經變成了空間中的數據這樣的問題,我們的存在的意義僅僅體現在績效、在那些適合時代的部分。只有適合時代,你才有生存的權利,你才具有這個時代生存下去的“外衣”。
我們今年沒有討論阿甘本的《神圣人》這本書,阿甘本還提出了一個概念,就是“赤裸生命”,被這個機制給排除出去。“規訓的人”是命運相對好的,雖然被規訓了,但是還有足夠的生存空間,能夠在社會中活下去,能找到你的位置:比如大家還能找到工作,在辦公室里有個飯碗,在格子間里天天碼字來賺點綿薄的收入。更慘的人是那些被判成神經病,判成不合群、情商低的人,這樣的人我們直接就把他淘汰掉了,他就變成了所謂的只能靠自己生命性身體來活著的人。
其實這個問題靠個體的防范是無解的,因為今天的人已經被高度生產為一個符合規范的人,你如果不符合規范,你自己心里會過不去:為什么別人能達到的我達不到?我們有個概念就叫“精神內耗”。實際上,人們就像是拼命地閹割自己,讓自己符合這個機器和裝置的運轉。同學們作為大學生,以后遲早要面對就業,有的考博士考碩士,有的要出國,但你們會發現全世界都是按照同樣的機制來玩游戲的,所以要學得“心態好”一點。我原來翻譯過巴迪歐的一本書,叫《何為真正生活》,他說只有兩條道路,一個叫拾級而上,按照裝置的既定規則來運行,雖然很艱難,雖然爬到某一步你就上不去了,但是可以一步一步往上爬,你會慢慢地獲得一些東西。還有一種是讓自己洇滅,就是說很多年輕人對這個世界不爽,選擇了各種各樣的陶醉,比如搖滾音樂、游戲,甚至吸毒,他們用這種方式來反抗巨大的機制。巴迪歐說了一句話,叫“飛蛾撲火式的反抗”,所以我們才說以個體去反抗是不成立的。要知道,馬克思當年在寫《共產黨宣言》的時候,從來沒有說個體的反抗是有價值的,一直說的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個體能動性在這里是微乎其微的,只是一種微光,不是沒有光,是有微光,但是微光很快就會熄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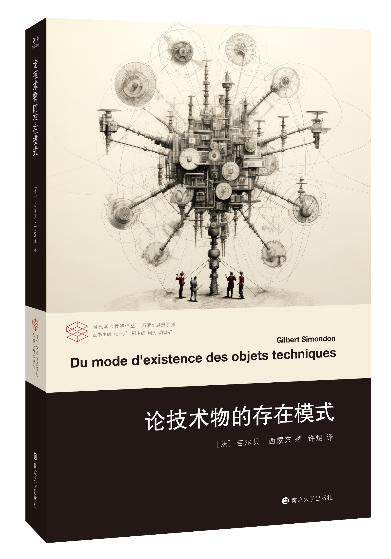
《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 [法]吉爾貝·西蒙東 著 ,許煜譯,南京大學出版社
技術物是人與世界的連接,它能夠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
西蒙東關于異化問題的討論出現在他結論的最后一章,可能針對的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關于異化勞動的討論。馬克思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針對的是整個私有制,書的全標題叫“私有財產與異化勞動”。他說造成我們異化的原因是,私有制把工人本來應該為自己生產的產品奪走了,這是一種剝削,造成了工人和自己的生產活動相異化。這里有四個相異化,第一是與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第二是與勞動生產過程相異化;第三,由于拿不到自己勞動過程的產品,人不能和勞動相統一,就造成了人和自己的本質相異化;最后是人與人之間的異化:有些人得到產品變成了統治者,有的失去了就變成工人階級被治理。這就是馬克思討論的問題。
那么西蒙東討論的核心問題是什么呢?他首先是承認馬克思的經濟計劃,但他所理解經濟計劃,還不能夠真正解決異化問題,這是西蒙東談異化問題的一個很重要的說法。西蒙東在一定程度上是認可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概念的,但他說這還不夠,再進一步分析本質就是人和技術物的彼此分離,這個分離并不是說工人沒有使用技術物,而是工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使用技術物。技術物是技術物,人是人,人并沒有在操作上和技術物聯合在一起。機器規定了一種運行模式,工人要被動地適應機器的節奏去運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卓別林在《摩登時代》里那種動作,機器有多快,你動作就得有多快,不可能按照自己習慣的節奏去運作機器。西蒙東在這里做了一個結論,不僅工人被異化了,機器本身也異化了。他認為這個原因出在工人與機器的分離,工人沒有資格去調試機器,因為機器的所有者是資本家。正常人和機器合拍的話,工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身體節奏隨時調試機器,機器也應該是和人結合起來、產生最大程度的連接,才能發揮它最好的效果,這才是人機合一,這個時候技術物和人才都不被異化。這中間多了一個私有制的關系。
我們怎么去理解技術物?剛才已經講了,技術物是我們人和自然環境、和周圍環境要素的連接方式。最理想的方式,當然是我們每個人通過技術物和所有東西來建立聯系。再舉個例子,比如手機肯定是技術物,但這個技術物是指什么?是外殼和屏幕這些物質材料構成的東西嗎?當我們使用手機時我們使用的是什么?大家想過這個問題嗎?我們打開手機的時候是打開微信、QQ、支付寶,打開各種各樣的應用,這些東西不在手機里面,而是通過手機連接到外面的某個網絡中去,我們使用的其實是網絡。
歸根結底,我們使用的不是技術物的物質材料,而是它將我們和世界連接起來的方式。再比如我們講智能汽車,大家都見過,現在的車一般帶一個屏幕,可以智能駕駛、掃描環境,那些東西就是一輛汽車嗎?人不坐進去,它還叫車嗎?我們很少說哪個人買了一輛車,是買了一個鐵殼子或者發動機回來。其實不是的,車的存在一定與它的遞接環境有關。車在路上行駛,它不是一個單純的物質,它與各種交通環境、與其他車、與各種信號、各種交通路標,比如紅綠燈、環形島、立交橋,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只有開在路上與別的車進行交互的時候,它才真正叫做車,停在車庫的那叫收藏品。而且在智能駕駛的時候,還要和背后的平臺聯系,比如說無人駕駛策略,是它掃描了環境,交給中央平臺處理調配的,中央平臺調配的不只是一輛車,它會給各種車發出指令。所以說,當我們坐到車里那一刻起,我們就通過這臺車和其他的車發生了關聯,建立了聯系。我們交流的不是車,而是通過車和一個更大的物質環境、社交環境聯系在了一起。其實任何技術都是這個性質。
同樣,無人機僅僅是一架飛機嗎?我們知道在戰爭里,無人機很重要,它提供了一個遙感視角,比如以色列是通過無人機發現辛瓦爾的,這個地方原本是不可能通過望遠鏡或者其他偵察設備進入的,但無人機進去以后,就可以把原來人類所觸及不到的環境建立在中間,它的中央指揮部就可以把這個環境捕捉出來,然后捕捉它所需要的對象。無人機就是一個技術物的典型概念,通過這個技術物,你會發現你進入了一個更大的世界,或者更不一樣的世界,這是技術物的關鍵。當你能與這樣的世界打交道的時候,整個思維都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現代社會的組織方式:通過技術物來控制規訓的人
雖然今天我們讀了兩本很老的書,《規訓與懲罰》是上世紀70年代的,《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是60年代的,但這兩本書在我們今天的時代都是有回聲的。《規訓與懲罰》里,福柯講的全景監獄就發生在人們身邊,每個人實際上都是一個全景社會的犧牲品,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感到不爽,但也感到反抗是無能為力的,因為只有按照這個機制走,才有希望。我覺得《黑神話》這個游戲編得很好,大家記得中間動畫里,悟空跟牛魔王說了一句什么話?“現在留給我們的道路就只有取經一條路,哪有我們反抗的路?其他路都被堵死了,只有老老實實取經才是你的生路。”大家讀到這里是什么感覺?實際上這就是現代人的誕生,把那些不可控的、不可預測的東西全部排除在外,人變成數據以后才可以在電腦模型中被預測,你的所有行為都可以被控制。把所有的風險和不可預測性降到最低,這是現代社會治理術的一個關鍵。
再回到技術物的問題,技術物和被規訓的人,或者被控制的人,是高度聯系在一起的,現代社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技術把這些人的空間整合起來。比如今天我們有人不用微信,我們很難聯系到他,就控制不了他,可過一段時間我們就把這個人忘了,這個人就相當于不存在(inexistence)。今天這個社會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技術物把我們連接在一起,組成了一個更大的巨型的行星級別的網絡,每個人都必須要通過技術物中介到里面,這也是我們個體化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