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興和議(1164年議定,1165年生效)達成后,宋對金稱侄,年輸歲幣銀絹二十萬兩匹,宋金兩朝由此進入了四十年的和平共處時期。四十年間,宋金雙方往來使節不斷,有“賀正旦國信使”,于每年正月初一向對方皇太后、皇帝或皇后致禮,有“賀生辰國信使”,向對方的皇太后、皇帝、皇后祝賀生日,其他臨時性的使節更難于統計。一方使者過淮河,踏上對方的土地,對方還有專門的接伴使接待,伴送進京,差畢,亦有送伴使送至淮河渡口而別。四十年間,不知有多少位雙方官員奉差出使,再加上接伴、送伴使者,道路相望,絡繹不絕。
乾道六年(1170)年,范成大受命為祈請國信使出使金國,當年六月,范成大啟程出京,八月渡淮,金朝一方的接伴使副已在淮河北岸等待,他們是正使尚書兵部郎中田彥皋,副使行侍御史完顏德溫。出使歸來,范成大作《攬轡錄》,記錄行程見聞甚詳。
陸游讀到范成大此書后,曾作詩《夜讀范至能〈攬轡錄〉言中原父老見使者多揮涕感其事作絕句》: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遺老不應知此恨,亦逢漢節解沾衣。

陸游
18年后的淳熙十五年(1188),十一月,楊萬里受命為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次年正月,又作為送伴金國賀正旦使,往來淮河一線。當年的淮河是宋金雙方的界河,中流以北即是金國國境,兩岸人民咫尺天涯,行舟不能越界,只有河水波痕交疊,飛鳥自在來往,無人管束。有感于此,楊萬里作《初入淮河四絕句》,其一: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干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二:劉岳張韓宣國威,趙張二相筑皇基。長淮咫尺分南北,淚濕秋風欲怨誰?其三:兩岸舟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為。只余鷗鷺無拘管,北去南來自在飛。其四:中原父老莫空談,逢著王人訴不堪。卻是歸鴻不能語,一年一度到江南。
陸游、范成大、楊萬里都是南宋著名的詩人,其中陸游年長,生于1125年;范成大其次,生于1126年;楊萬里又其次,生于1127年。三人年齡接近,都是一時才俊,頗負時譽,彼此關系也非常親密,他們交流作詩心得,互贈詩集,互為詩集作序跋,以詩唱酬更不在話下。淳熙二年至四年(1175-1177),范成大在成都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陸游為制置使司參議官,兩人在成都共事三年,“以文字交,不拘禮法”,更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紹熙四年(1193)范成大去世,陸游痛失老友,作《夢范參政》詩哭之:平生故人端有幾,長號頓足淚迸血!范成大享年六十八歲,這時的陸游和楊萬里兩人,也都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先后進入了半退休的狀態。
紹熙五年(1194),宋光宗趙惇因病不能視朝,宗室大臣趙汝愚、外戚韓侂胄擁太子趙擴即位,從此,南宋政治進入了韓侂胄弄權、專權的時代。
韓侂胄的傳記在《宋史·奸臣傳》中。慶元四年(1198),韓侂胄拜少傅,封豫國公,次年遷少師,封平原郡王,再次年,進太傅,嘉泰三年(1203),拜太師。不數年間,韓侂胄權傾一朝,為所欲為,“群小阿附,勢焰熏灼。侂胄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陳)自強至印空名敕札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
大權在握,韓侂胄雄心勃勃,想大干一場,立萬世功業。“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于是恢復之議興”。天下最大的功業莫過于“恢復中原”,韓侂胄決定發動針對金朝的北伐戰爭。嘉泰四年(1204),在韓侂胄的建議下,南宋追封此前已經平反昭雪的岳飛為鄂王,開禧二年(1206)又削去秦檜所封王爵,改謚“謬丑”,以此來為北伐造勢。
開禧二年,史稱“開禧北伐”的戰爭爆發了,在韓侂胄的總運作下,宋軍發動進攻,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慶攻取泗州及虹縣,江州統制許進攻取了新息縣,光州孫成攻取了褒信縣。“捷書聞,侂胄乃議降詔趣諸將進兵”,隆興和議達成四十年后,宋金兩朝再度爆發大規模戰爭。
十多年來,韓侂胄弄權奪權,打擊政治對手,培植了大量黨羽,同時也樹立了大批政敵,這些政敵反對韓侂胄的專權,當然也反對韓侂胄挑起的這場戰爭,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朱熹。曾經王淮為相,王淮向楊萬里征求人才,楊萬里“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朱熹1130年出生,僅比楊萬里小三歲,但在仕途上曾得到楊萬里的推薦,兩人反對韓侂胄的態度,也是一致的。
不過,對韓侂胄主持發起的北伐戰爭,晚年的陸游卻曾非常期待。戰爭爆發的這年,陸游已是八十歲(虛歲)高齡,他退居故鄉山陰(今浙江紹興),雖遠離朝廷,但無時無刻不關心天下大事。嘉泰四年(1204),時任浙東安撫使兼知紹興府的辛棄疾奉召入朝,陸游意識到這一定和準備打仗的時局有關,因此作長詩《送辛幼安殿撰造朝》相送,預祝辛棄疾此去,率千軍萬馬,北定中原,為國家立功,名垂青史:……天山掛旆或少須,先挽銀河洗嵩華。中原麟鳳爭自奮,殘虜犬羊何足嚇。但令小試出緒馀,青史英豪可雄跨。……
一天風雨大作,陸游困居家中,但聽傳聞,好消息不斷傳來,說是四川的糧船已經抵達前線,宋軍糧草充足,后勤無憂,旗開得勝,已傳檄下百城。陸游非常激動,希望自己晚死片刻,能等到宋軍大獲全勝的那一天,因此作《五月二十一日風雨大作》一詩:風雨縱橫夜徹明,須臾更覺勢如傾。出門已絕近村路,對面不聞高語聲。銜舳江關多蜀估,宿師淮浦飽吳粳。老民愿忍須臾死,傳檄方聞下百城。
可是,宋軍的軍事行動很快遭到金軍的強烈反擊,優勢瞬間轉為劣勢,在唐州、城固、宿州一線,宋軍先后大敗,金軍乘勝追擊,宋軍一潰千里。“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真、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金軍大舉渡過淮河,攻入了宋朝的地盤。
此時的韓侂胄,如夢初醒,趕緊派人與金人談判求和。“金人答書辭甚倨,且多所要索”,“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為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戰局有利的金人,在談判桌上開出了高價:一是索要四十多年前欠納的歲幣,二是將金軍所到之處劃歸金朝管轄,三是索賠軍費銀數千萬兩,四是抓捕懲辦挑起戰爭的罪魁禍首。這樣的條件,特別是最后一條,韓侂胄當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復銳意用兵”,決心將戰爭繼續打下去。
面對敵軍壓境,韓侂胄一意孤行,宋朝內部朝野異議不斷,事實上也面臨著許多具體的困難,史書所謂:“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
既然金人要求懲辦首惡,韓侂胄就成了結束戰爭的關鍵,韓侂胄的政敵們開始謀劃除掉韓侂胄,在這些人的積極活動下,宋寧宗趙擴決定拋棄韓侂胄,他發出密詔,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兇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
密詔發出,解決韓侂胄的問題就在眼下,為防意外,又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加強防護。第二天一早,韓侂胄正常上朝,大轎子剛剛靠近宮殿區外面不遠,夏震上前攔住了韓侂胄,“(夏)震呵止于途,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韓侂胄被刺殺身亡,一件令皇帝焦慮滿朝束手的大事,就這樣被一個小人物瞬息之間解決了。次年,“金人求函侂胄首”,朝廷命臨安府安排,派人斫開了韓侂胄的棺木,取韓侂胄首級函送金國。對于韓侂胄發動的開禧北伐,宋寧宗曾有評論說:“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
韓侂胄死在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陸游十二月間有《雀啄粟》詩,對韓侂胄及其黨羽僥幸得到權力最終取敗的下場,表示了諷刺或遺憾:坡頭車敗雀啄粟,桑下餉來烏攫肉。乘時投隙自謂才,茍得未必為汝福。忍饑蓬蒿固亦難,要是少遠彈射辱。老農輟耒為汝悲,豈信江湖有鴻鵠。
此時,陸游的老朋友楊萬里也已退休多年。韓侂胄用事,曾欲網羅四方知名人士為自己造勢,因私家園林南園建成,韓侂胄曾請楊萬里為之作記,試圖以此籠絡楊萬里。楊萬里答復:“官可棄,記不可作也。”楊萬里拒絕與韓侂胄合作,“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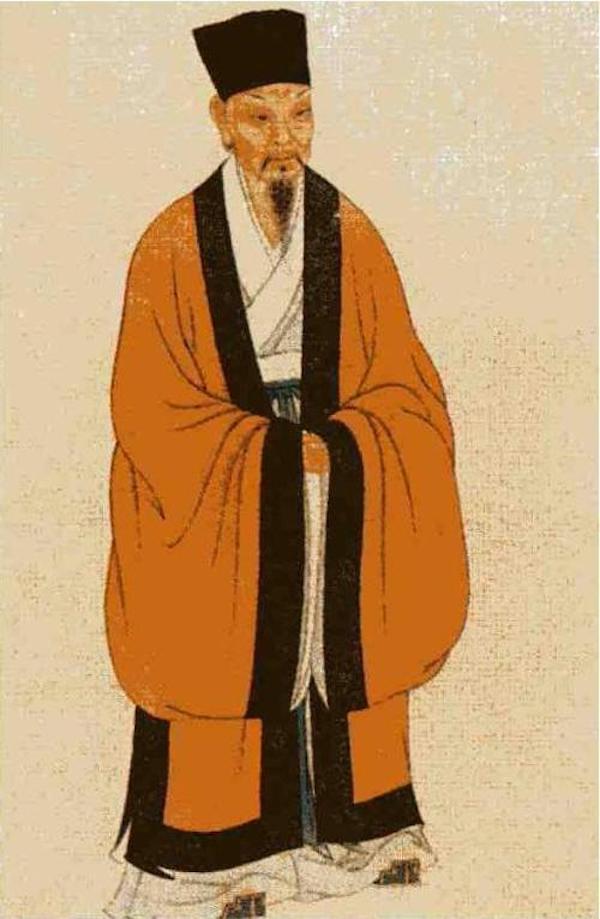
楊萬里
眼看韓侂胄專權橫行日甚一日,楊萬里憂憤不已,怏怏成疾。家人知道他的心情,怕他過分擔憂損害健康,因此盡量為他屏蔽來自朝廷的消息,“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但意外還是發生了,一天,楊萬里的一位侄子來家,一進門就說起了戰爭爆發的事情,楊萬里聽罷大驚,“慟哭失聲”,他命人拿來紙筆,寫下遺墨數行:“韓侂胄奸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可以說,楊萬里是被韓侂胄的胡作非為氣死的。
關于楊萬里的死,由其子楊長孺、楊次公、楊幼輿撰寫的《請謚狀》記錄得更加詳細生動,該文可見楊萬里文集《誠齋集》卷一三三所載太常博士陳貴誼、考功郎官李道傳《謚文節公告議》的引述:“開禧元年,歲在乙丑,孟秋之月,(楊萬里)慨然上奏,極陳侂胄之奸,竟以壅閼,不得自達而止。開禧二年,歲在丙寅,侂胄矯詔生事,開邊釁,啟兵端。臣等家人,知先臣萬里憂國愛君,忠誠深切,而又老病,恐傷其心,凡聞時事,皆不敢告。忽有族侄楊士元者,端午節自吉州郡城書會所,歸省其親,五月七日來訪先臣萬里。方坐未定,遽言及邸報中所報侂胄用兵事。先臣萬里,失聲慟哭,謂:‘奸臣妄作,一至于此!’流涕長太息者久之。是夕不寐,次朝不食。兀坐齋房,取春膏紙一幅,手書八十有四言……既書題畢,擲筆隱幾而沒,實五月八日午時也。”
楊萬里的臨終手跡,后人們不敢公布,只得“泣血收藏”,因為該時仍是韓侂胄掌權期間,“侂胄氣焰熏灼,生殺自肆,鉗制中外,道路以目”。楊萬里的兒子們“上則恐貽老母之憂,下則懼為家門之禍,深思熟慮,塞口吞聲,抱恨茹哀,不敢赴訴”。內心以為父親堅決與韓侂胄作斗爭的忠君愛國之心,永遠不能大白于天下了:“自謂先臣萬里,赍志九泉,銜冤千載,忘身殉國,此意莫明。不肖諸孤,甘受不孝之罪,已矣,無可言者矣!”
讓楊家人萬萬料不到的是,次年年底,韓侂胄即被夏震殺死,函首金國,余黨全部被清算,楊家聞訊,歡欣鼓舞:“誠不自料,先臣萬里亡之后,未及兩年,天日清明,奸臣竄殛,英斷奮發,薄海歡忻,天憫神恫,賜此幸會。先臣萬里之志,于是時而可明,先臣萬里之冤,于是時而可白。闔門老幼,哀號躃踴,遙瞻天闕,仰吁天聰。”于是將楊萬里去世前后的詳情報告朝廷,將楊萬里的臨終遺墨附錄于前,請皇帝開恩“宣付史館”,表彰事跡,并請皇帝賜謚號:“謹以先臣亡沒之由,具狀奏聞,仍以先臣萬里遺囑刻石碑本連粘在前,隨狀上進。欲乞圣慈特賜睿覽,將上件事跡,宣付史館,使先臣萬里遺忠大節,暴白于天下后世。臣長孺,臣次公,臣幼輿志愿畢矣。孤苦余生,死不恨矣!”不久,楊萬里被賜謚“文節”。
與楊萬里拒絕與韓侂胄合作的態度不同,晚年的陸游曾一度將恢復的希望寄托在韓侂胄的身上,為表示對韓侂胄的支持,他為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因此被輿論批評,“見譏清議”。朱熹曾評論陸游:“其能太高,跡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朱熹的這句話被寫進了《宋史》陸游的傳記中,于是,陸游的“晚節”問題,似乎真的成了問題,八百年來,不時被人提及。其實,八十多歲的老人陸游哪里是在支持韓侂胄,他只是在支持他一生夢寐以求的恢復事業而已。
1210年陸游去世,享年八十六歲。臨終前,陸游寫下了那首家喻戶曉的《示兒》詩: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